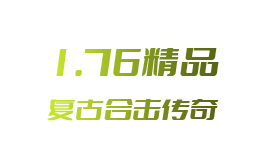
桑葚
在临江市场后面的小巷里,一个手掌粗糙的农妇把手里的篮子一放到路边,我的眼光便被拉过去了。随着她弯腰的身影,我蹲了下去。女人的篮子满满装着桑葚,它们一颗颗乌黑发亮安静挤靠在篮子里,像一堆熟睡的蚕蛹,蜷起
在临江市场后面的小巷里,一个手掌粗糙的农妇把手里的篮子一放到路边,我的眼光便被拉过去了。随着她弯腰的身影,我蹲了下去。女人的篮子满满装着桑葚,它们一颗颗乌黑发亮安静挤靠在篮子里,像一堆熟睡的蚕蛹,蜷起身子做那化蝶的美梦。女人的手里拿着个带把的小搪瓷缸子,是要用它一杯杯将桑葚舀进买主的塑料兜里。再细看她的十指,指甲缝里嵌满了黑色浆液,一定是早起树上摘桑葚留下的痕迹。
“多少钱?”我问。
她讷讷报出数字,竟是意想不到的便宜。我递过两元钱,换回一大兜桑葚。回到家里,桑葚带些土腥的气味直往鼻子里钻,没引出肚里的馋虫,倒勾起了我对“桑葚”的回忆。
桑葚在我的家乡又叫“桑果子”,记得幼年时,母亲教书的那个乡镇,因农户皆以蚕茧为副业,田间地盖遍植桑树,每到初春,桑葚特多,而且果大肉厚,每到季节,孩子们争相采食,个个弄得手嘴鸟红。记得母亲曾对我和妹妹说:桑葚是可以吃的,但因有蚂蚊和昆虫爬食,要采集回家洗净,不然要得病的……。后来我和其他孩子先采集后,交给妈妈用盐水浸洗,然后—人分得—小碗,在嘻嘻哈哈的笑声中,吃得满嘴鸟红……。吃桑葚成为幼年贫困岁月最珍贵的记忆!
我对桑葚的另一个记忆则是上世纪六十年代初,我分配到江油—所乡镇中学教书,那时正值生活紧张,人人饥肠辘辘,桑葚已是稀罕之物,农村须由生产队统一采集,交国营酒厂酿酒,记得那年中秋节,每个教师统配了半斤“桑葚酒”,酒味酸甜,呈乌红色,乙醇含量约30度,教师们一人分得半碗,—位理化老师品尝后调侃说:别小看此物,乙醇经消化系统可以直接转化为葡萄糖,可补充一千大卡热量……。教师们均视为珍品,一饮而尽,我当时从未沾过酒,下肚后竟然微醺,有些飘飘然起来……,此事至今记忆犹新。
然而桑葚中也有特殊的另类叫“马桑葚”,生长在一种叫马桑树技桠上,马桑树被家乡的农民称为“马桑拐子”,山里杂草乱树中少不了大蓬“马桑拐子”的身形——没去考证它的学名,家乡人都这么叫它。它低低矮矮的,所有枝桠全都横七竖八杂乱地伸展,看去像是懒汉在四仰八叉躺着。不说盖房子,它歪歪扭扭的树干连做扁担也不够格。“长得歪拐六斜的,就和那马桑拐一样!”山里人时常这样嘲笑那些形貌丑陋者;“你娃儿!就是那马桑拐子——不成材!”大人们咬牙切齿教训不学好的儿郎。
这马桑拐子的果实就是马桑葚,它色艳形美,很容易和桑葚混淆。初春时节,山花遍野,马桑拐青青的叶间便密麻麻结出马桑葚,熟透的则紫红得耀眼。引诱得山里饥肠辘辘的孩子们争相采食。然而马桑葚不同于桑葚,它有着不小的毒性,吃多了也会致死。山民们积累长期与大自然周旋的经验,看到哪个孩子因食用马桑葚而不慎昏迷,便舀一小瓢大粪,撬开紧闭的嘴灌下去。—番呕吐,一时三刻,中毒的孩子便又活蹦乱跳了。即使如此,在贫穷饥荒的岁月,孩子们经不住马桑葚的巨大诱惑。每年村里都有被拖去抢救的孩子。
去年到家乡农村走亲戚,看到退耕还没来得及还林的光秃秃山坡上隐没着几棵马桑拐没精打采的身形,枝上还稀稀拉拉点缀些泛红的果子。当我指着它询问怯怯走在我身边的几个山里孩子:“有没有吃过它们?”他们摇摇头,眼里是迷茫的表情。看来,我手里的桑葚也好,山上仍生长着的马桑葚也罢,将野果子当作山珍的时代早已远去了。幸甚!
版权声明:本文由1.76精品复古合击传奇发布网原创或收集发布,如需转载请注明出处。
相关文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