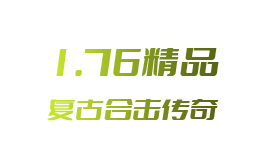
门外品艺
一、戏曲山西梆子绵长的拖腔,似能渗到骨髓里去。委婉熨帖,欲落不落,尽尤未尽,听起来有一种令人心酥的酣畅。蒲剧中的降7,在琴弦上那么轻轻一揉,人生的悲凉与酸楚就现出了缠绵的温婉,那是属于北方人优雅的伤感
一、戏曲山西梆子绵长的拖腔,似能渗到骨髓里去。委婉熨帖,欲落不落,尽尤未尽,听起来有一种令人心酥的酣畅。
蒲剧中的降7,在琴弦上那么轻轻一揉,人生的悲凉与酸楚就现出了缠绵的温婉,那是属于北方人优雅的伤感。
越剧的柔,则是要把人心泡进消魂蚀骨的温泉里,轻轻款款地搓捏一番,令你如饮薄酒,如沐微风。
京剧高亢激越,像是大块文章,洋洋洒洒、铺天盖地,有着官样的气派,铺排夸张,火辣辣地,气度不凡。
评剧似说似唱,先叹一口气,告诉你:唉——提起来——话长——是“花开两朵,各表一枝”的味道。用老百姓的口吻平心静气,娓娓道来,讲那么一个故事,一段传说,多是家长里短的话题。
河南梆子则是中原人“侉”气的典型体现,越“侉”越有味儿,只需品一下豫剧的风格,就能多少窥出一点河南人的特点:平实、明朗、爽快,辣中多少有点酸,却酸得恰到好处。那唱腔一口甩出来,像是冬日里的一碗酸辣饺子汤。
山东梆子,豪气直上干云霄,一开口就是“一百单八将”,打杀之气,好汉性情一览无余。
中国戏曲品种繁多,味道各别。人在年长之后,大多酷爱家乡戏,推敲起来,盖源于一种“剪不断,理还乱”的乡情。这份情是对童年的难以忘怀,是对乡音土语刻骨的眷恋,是亲人的音容笑貌,是老屋前的一棵古槐,是水井边的一条小路……。把这种归根情结织在一种从小听惯了的旋律中,难分难解。于是,家乡戏就成了一种慰情的象征,一种只有自己的心才能品咂出来的滋味,说到底是源自一种深刻的爱。
二、歌曲
流行歌曲从极富人情味儿的柔糜到人工煽情的狂呼怒吼,再到无话可说,无情可抒,平铺直叙,似唱似年似唠叨,表现出了现代人感情的苍白、罄干、枯竭。几乎成了完全的词汇大拼盘。什么叫“何惧风流”?“朝花夕拾”和“杯中酒”又有什么关系?连“爸爸妈妈你们好吗”也能入乐,没有什么东西不可以谱曲的了。如同任何一个人都可以扯起嗓子放歌卡拉OK一样,艺术和生活已毫无界限。“纤夫的爱”里,“小妹妹”大叫大嚷着要“让你亲个够”,令人汗毛倒竖。
同样是情歌,意大利的《桑塔*露琪亚》同样也不够含蓄却颇耐人寻味。第一段结尾道:“在这黑夜之前,请来我小船上,桑塔?露琪亚,桑塔?露琪亚。”第二段结尾道:“在这黎明之前,快离开这岸边。桑塔?露琪亚,桑塔?露琪亚。”至于来到小船上干什么了,却只字不提。对情人的爱,不是用“泪水肚里流”来表现的(这大概是所谓“中国式的爱”,却又显得太不现代)。只是反复吟唱她的名字。和中国人一样,因为是“幽会”,所以怕人看见,要她在黎明之前,快离开岸边。短短两句,其内涵要比“让你亲个够”丰富的多,却不让人觉得露骨,简洁直白又蕴意无穷,给听者留出了充分的想象空间。
同样的例子还有中国的新疆民歌《擦皮鞋》,旋律简单,歌词质朴,道:
那天我从你家门前过,
你端着(那个)洗锅水往外泼。
泼到了我的皮鞋上,
过路的人们笑呵呵。
你什么话也没有对我说,
瞪着两只眼睛望着我。
我不愿擦去这鞋上的泥,
只因为是你亲手泼。
每当我看见这鞋上的泥,
你的影子就从我眼前过。
这件事我一直也放不下,
不知道你想我不想我。
白话一般,短小精干,却把一个完整的故事,一种微妙的心态,一种难以释怀的“一见钟情”,用老百姓的语言,生动、活泼、立体、朴素地表现了出来,给人以强烈的感染,会心的微笑和丰富的联想。
现代流行歌曲中,也有个别极富艺术感的,如《涛声依旧》。歌曲旋律平庸,缺少深沉优美的抒情色彩,歌词却写得令人回肠荡气:“月落乌啼总是千年的风霜,涛声依旧不见当初的夜晚”。唐人张继的《夜泊枫桥》被揉的很得体,实乃为今人和古人在同一轮明月下不同情感的不同喟叹,这种差别中的和谐,营造了一种浓浓的文化氛围。听来令人怦然心动。可惜这样的好歌词实属凤毛麟角。而好词好曲的珠联璧合之作,更是几乎空白,至于像“高高山上一棵槐,手攀槐枝望郎来,娘问女儿你望什么?我望槐花几时开”一类纯情、泼辣、真挚、热烈的民歌传统,也被遗弃的不知所终了。而今所谓的“民歌风”,好比大都市里的新式“古建筑”,去其精华,留其糟粕,粗制滥造,不伦不类,非驴非马,毫无“品质”可言。如:“大姑娘美,大姑娘浪,大姑娘走进青纱帐”,粗俗不堪,竟还搬到了某年某地的春节晚会上。
文化已随风逝去,触目周遭,值得玩味的东西实在无多。
三、歌剧
标志了一个时代的中国歌剧,很有特色,那特色是民歌与地方戏的结合,可惜没有得到很好发展。旧有的剧目都已成了历史标本,一如“样板戏”,只对有“怀旧”情结的中年人释放魅力。
歌剧从不曾跳出戏曲的影响,到后来的《骄杨颂》也一样有着湖南花鼓、浏阳民歌、井冈山民歌的风格。再后来的《宦娘》、《伤逝》,虽然借鉴了外国歌剧的手法,很经典,很意大利,但因缺少了文化的根基础,没有造成什么影响就销声匿迹了。远离大众欣赏水平的艺术作品,一如爱情中的单相思,只能自己说给自己听。
《江姐》、《洪糊赤卫队》、《红珊瑚》可以说都是戏的变种,而且大都以地方戏和民歌作基调(如同现今的文艺杂志起刊名,山西有《汾水》,陕西有《延河》、洛阳有《牡丹》)。典型的要数《江姐》,其中的“粉碎你旧世界……奴役的锁链……”紧拉慢唱。鼓板“吧嗒吧嗒”,乐队“5656”,整个戏曲用法都搬过来了。中国有地方戏,也有地方剧。
主要以民歌为音乐素材的,是《小二黑结婚》,多数唱段几乎是原调照搬,小二黑唱“这次大会真热闹,全区的代表都来到”,纯粹的祁太秧歌(二人台?)小芹对二黑哭诉“二黑哥……今天媒婆子到我家”,典型的襄垣秧歌甩腔,最后一场,区长和刘修德、三仙姑对唱:“你就是刘修德?”“区长就是我”……“你要把小芹嫁给谁?”“姓吴的,住在那吴家庄”,是地道的上党鼓书。这部歌剧虽然将山西境内的“土特产”全部吸收了,却消化的不好,显得十分杂碎和零乱,对音乐素材的生吞活剥使风格散漫,不够协调(请内行的读者恕我在此斗胆批评马可老前辈)
版权声明:本文由1.76精品复古合击传奇发布网原创或收集发布,如需转载请注明出处。
上一篇:游天台山记(五)
下一篇:你在前,我在后,理智在中间
相关文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