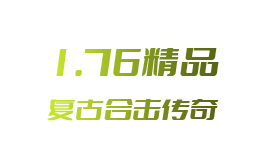
怀念母亲
再过几天,就是母亲去世一周年的忌日了。这一年来,我发疯似地思念着母亲,几乎每晚睡前都祈祷着母亲能来入梦,以解女儿的思念之苦。而每次在梦中与母亲相遇,都与她老人家活着的时候一模一样的,妈妈的音容笑貌,举
再过几天,就是母亲去世一周年的忌日了。这一年来,我发疯似地思念着母亲,几乎每晚睡前都祈祷着母亲能来入梦,以解女儿的思念之苦。而每次在梦中与母亲相遇,都与她老人家活着的时候一模一样的,妈妈的音容笑貌,举止言谈,都仿佛刀刻斧凿一般铭刻在我的内心深处,任什么都无法将母亲的印迹抹去。妈妈!如果有来世,您就来当我的女儿吧,我多渴望能像您疼爱我那样来疼爱您啊!除了您来当我的女儿,我想再也无法将您给我的爱回报给您了!我是妈妈四个儿女中最小的一个,妈妈叫我老丫头。我是妈妈35周岁那年生的,那时候还没时兴计划生育,但听妈妈讲,生完我,爸爸和妈妈就决定不再要孩子了.也许老人都会对最小的孩子偏疼偏爱些吧,我从小就受到爸爸妈妈更多些的疼爱.虽然当时并不觉得有什么,但长大后,细细想来,还真的是这样.比如爸爸,我的哥哥姐姐他都打过,却唯独没打过我;妈妈对我的爱就更是无法言说了.我懂事后,觉得与妈妈的感情更好像是相依为命,尤其是我们家下乡插队的那段日子和妈妈年老之后.母亲对我的爱,从我小的时候就常常被感动得泪流满面,那种从心底产生的痛楚般的爱恋,我想,没有相同的经历的人,是无法理解的.
1970年的春节前夕,我和妈妈随父亲插队落户到桓仁山区.之所以只有我一个孩子跟父母去下乡,也是因为我是老孩子.那时候姐姐已结婚多年.两个哥哥也已经成为知识青年了.父亲从五七干校的"牛棚"里一出来,就被转为"五七"战士了,那时候五七战士下乡讲究"五带":带户口,带粮食关系,带党籍,带工资,带家属,大概就是这"五带"吧,我和妈妈就是"五带"之一:家属.那年我十五岁,妈妈则刚好五十岁.
说到跟父亲插队的日子,应该先介绍一下我的父亲。
我的父亲和母亲同是黑龙江省通河县人士,父亲从小身体不好,因为我的亲奶奶怀着父亲的时候就一直卧床不起,生下父亲后不到一年就去世了。父亲常说自己是先天不足,后天更亏损,因此体质十分虚弱。那时爷爷家开了个鞭炮铺,其实也就是勉强糊口而已,只是因为父亲体质太差,干不了什么出力气的活儿,所以爷爷就想方设法送父亲进了学堂去读书了,指望他日后能靠笔杆儿混口饭吃。谁能料到,父亲干活不行,读书却相当了得!门门功课都名列前茅,年年都得全额奖学金,他成了家乡小镇的骄傲!父亲读书最后读到“国高”毕业,现在的年轻人不知道“国高”是什么样的学历,上了年纪的人却都知道,能念到“国高”,真算得上是那个时代的“文化人”啦!可真是应了那句古训了:塞翁失马,焉知非福?父亲成也在读书,败也在读书。决定父亲命运的事情,都发生在读书期间了。
父亲念国高时,正是抗日战争时期,那时候学生中有进步青年,也许就是党的地下工作者吧,在学校里从事抗日救国的宣传游行等一系列的活动。父亲也正是血气方刚,也有正义感,您说哪个中国人能愿意当亡国奴呢不是?所以,年轻人聚到一起,只要一谈起国事,谁也都是义愤填膺,慷慨激昂。那时的父亲,根本不知道自己的人生会因为此种情形付出什么样的代价!
但后来真的出事了!
在一次学潮之后,不少参与活动的学生都被当局抓了起来,包括父亲在内,但父亲只被训问了一些诸如为什么不好好读书而要去闹什么学潮之类就放出来了,父亲的大多数同学都是这样问过之后回到课堂就以为没事儿了。那时他们都不知道到底发生了什么。几十年的光阴一晃就过去了,父亲也是因为有文化,进入了支援辽宁的工作队,在银行系统工作。父亲果然是靠笔杆端上了国家的“铁饭碗”。在我们国家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中,父亲被关进了牛棚,被莫名其妙地不断地训问当年闹学潮的事情,被明着暗着逼迫着让坦白当年背叛革命,出卖同志的罪行。父亲是在被反复地让坦白、承认的过程中,一点一点地才知道了当年的真实情景,那就是在学潮中,党的地下工作者被逮捕了,组织上认定父亲就是那个出卖同志的叛徒!也就是说,如果这个结论是真实的,准确的,那么父亲在国高读书时就已经是共产党员了!
知道这个罪名有多严重吗?
父亲当然据理力争。
我在国高读书期间就已经是共产党员了吗?谁介绍我入的党?履行手续了没有?
组织也不清楚。但组织把这个问题做为历史遗留问题挂在了父亲的头上。父亲就是带着这个遗留问题踏上了五七道路的。父亲当时51岁。还没有现在的我大。
我母亲娘家姓马。按照老家的习俗,女人出嫁后就被冠以夫姓称呼。我们家姓初,所以出嫁的母亲被娘家人称为“老初”。
说起母亲嫁给我父亲,还颇有些戏剧性。
母亲其实是姥姥家的三闺女,但后来我二姨去世了,母亲就成了事实上的二闺女了。姥姥共生了五女二男七个孩子。我姥爷是木匠,解放后被定为八级工匠啊,可真不简单呢,像姥爷那个年龄的人,哪有几个是吃公家饭的呢,姥爷就是。姥爷有退休金的。母亲其实是继承了姥爷的遗传了,一辈子要强,能干,什么困难都不放在眼里,什么苦都能吃。母亲当姑娘的时候,也曾进过私塾去读书,可她的弟弟----我的舅舅就坐在她的前座,舅舅小时候很顽皮,不好好读书,常挨先生的手板,舅舅倒没觉得怎么样,可母亲受不了了,她无法眼看着自己的弟弟因为读不好书天天挨先生的打,于是说啥也不去念书了。那时候的女孩子出嫁早,母亲当然也不例外,十五六岁的时候,媒人便进了门。那就是我爷爷派去的。小镇不大,谁的姑娘长得好,能干,谁不知道呢?母亲名马凤坤,人长得漂亮,针线活儿好,做衣服做鞋全不在话下,看她绣的花儿,看她做的鞋,你都舍不得穿呢。那年母亲刚十六岁。媒人说,老初家的长子,念着书呢,个头矮了点儿,但有文化呀,将来一准儿差不了!
姥姥问,有文化的人,不打人吧?
姥爷常在不满意姥姥的时候,随手拿起自己干木匠活的家什儿满村子追着姥姥打。
她可不想自己的女儿也跟自己一样,被丈夫追着撵着抱头鼠窜。
“打人?连骂人都不呢!”媒人颇为自豪般地说着。当娘的,先就同意了。就凭他不打人就行。
可母亲后来知道父亲有点踮脚,一个好好的姑娘怎么能愿意找个瘸子呢,就说啥也不同意这门亲事。怎么回事呢?原来是父亲念书时有一次踢足球,跟同伴踢对脚了,就是说,俩人同时
版权声明:本文由1.76精品复古合击传奇发布网原创或收集发布,如需转载请注明出处。
下一篇:白露未晞
相关文章
